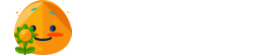如果你不會逼腳有殘疾的人奔跑,就不應該要求憂鬱症患者「看開一點」!

photos放大顯示
「我覺得生活每天都是從負的開始。」我的朋友K常常這麼說,說憂鬱的日子好難受,每天都在想著怎麼結束自己的生命。和K聊著聊著,也看了幾本精神疾患書寫的書籍,都有一種捨不得的心情。憂鬱之於人,為什麼可以造成一個人如此大的影響,即便在外人眼中的他們,是多麽的光鮮亮麗,是多麽的不應該憂愁?「但就是會難過,沒有理由。」她說。
面對這樣的人,真的好希望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亮麗的外表,伶俐的腦袋,加上一顆善良能夠同理別人痛苦的心,理當能夠為這個世界帶來祝福、為需要的人送上溫暖。「我好想,可是我做不到,我覺得很無力。」正因為比別人更能同理這世界的痛苦,她也感到痛苦。也許就像作家蔡嘉佳[註1]所說的:「很多人以為憂鬱症是厭世,其實,他們比任何人都愛這個世界。」
為什麼會有憂鬱症?
從K開始,我開始研究、閱讀和思考,為什麼人會感到憂鬱?為什麼人用了憂鬱症的藥物一定要有那麼難受的副作用?為什麼快樂不該屬於這樣溫暖的人?
從生物醫學的角度來看,大抵上是腦中的神經傳導物質(例如血清素)的量太少[註2],導致人感受不到快樂。
從心理的角度切入,憂鬱症可能是人傾向看到自己壞和差的一面,並在這樣低潮的情緒中,更容易聯想到許多負向的經驗,如此惡性循環。最後變得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思緒、自我價值感低落。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在身處的情境中得不到抒發、或是長期處於某種壓力、壓抑的狀況,而對於無法改變的現況的無力,讓這個情境中的人感到欲振乏力,最後可能在此情境下而有了憂鬱症。

photos放大顯示
憂鬱症的解藥?
現行醫療用了許多藥物,來刺激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或是讓它們存在大腦久一點,不要讓快樂的感覺那麼快消失。但是伴隨而來的,身體其他部位也有許多藥物會影響的受器,很容易帶來為數不少和不輕的副作用。簡單來說,抗憂鬱的藥物像是散彈槍,可以攻擊憂鬱症,但是也無意間傷害到自己。「我覺得我的腦袋開始變慢,我逐漸失去引以為傲的思考能力。」「我失眠,我感受不到情緒、我容易忘記東西。」K 說。
而在心理諮商方面,也有認知行為治療,從當事人的家庭、成長背景或是看待事情的方式逐步剖析,找到認知中糾結的某個點,並透過談話和一些練習帶領當事人去思考不同看待事情的方式。
現在憂鬱症的治療方式因人而異,選擇看精神科的會服用藥物治療;選擇諮商的會接受認知行為治療,也有一些用電療的案例存在。不過大抵上憂鬱症還是難以用單一方式完全治癒,雖然透過心理治療和藥物可以得到控制,但是在成效上每個人都不同。
社會對於憂鬱症的態度?
接下來談社會對於精神疾患的不友善。作家林奕含[註4]回憶道:從政大休學前,她拿著診斷證明,向系主任解釋為什麼沒辦法參加期末考,他回應道,「精神病的學生我看多了,自殘、自殺,我看妳這樣蠻好、蠻『正常』的,」系主任接著拎起診斷書,說出林奕含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9個字,「妳從哪裡拿到這個的?」
大眾其實對於精神疾患普遍不了解,甚至是大學教授可能也有對精神疾患的刻板印象。精神疾患其實看起來跟正常人沒有什麼不一樣,他們易碎的不是外表的模樣,而是內心。
當他們鼓起最大的勇氣,跟其他人坦承自己的精神疾病之後,換來的不是同理,反而是質疑與不了解。這樣負向的循環下,大眾越來越不了解精神疾患的內心和處境,精神疾患的人也越來越不敢跟他人坦誠自己的病情,一旦坦承了,就好像做錯事一般,不但沒有得到安慰,反而還會被人從頭到腳審視一遍,心想著:「怎麼可能?」但他們最需要的,其實是接納和理解,至少不要被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我們所學的,不要用一本書的封面而斷定書的內容,顯然沒有運用在對於精神疾患的了解上面[註5]。所以傷害更深、誤解更深。情緒沒有得到抒發,像是陳酒一般釀在心裡,久了,難過會烈到讓人失去理智、失去過去所有相信的價值。「死」常常是他們最好的開罐器。

photos放大顯示
對於憂鬱症,我們可以做什麼?
「結果找一個我信任的人還比治療師有效。我從來沒有和治療師坦承我的恨,你是第一個讓我說出來的人。」某天跟K聊完,她這麼跟我說。
以自身和K相處的經驗來說,我們其實很難幫憂鬱症的人做到什麼,但是陪伴絕對會是一種力量。因為陪伴的過程中,他們可以感受到你的善意和溫暖,願意把他們心裡的話跟你分享。這很重要,因為他們不再是一個人面對這世界對於憂鬱症的不友善。
除了陪伴之外,我們也可以看看精神疾患寫的書籍,了解到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還有遇到的困境與掙扎是什麼。或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切入點,雖然沒辦法為他們平反所有不友善的事情,但至少我們能夠透過書籍去同理他們的心情和處境。理解和同理,會是社會對憂鬱症友善的第一步。

photos放大顯示
「我覺得生活每天都是從負的開始。」我的朋友K常常這麼說,說憂鬱的日子好難受,每天都在想著怎麼結束自己的生命。和K聊著聊著,也看了幾本精神疾患書寫的書籍,都有一種捨不得的心情。憂鬱之於人,為什麼可以造成一個人如此大的影響,即便在外人眼中的他們,是多麽的光鮮亮麗,是多麽的不應該憂愁?「但就是會難過,沒有理由。」她說。
面對這樣的人,真的好希望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亮麗的外表,伶俐的腦袋,加上一顆善良能夠同理別人痛苦的心,理當能夠為這個世界帶來祝福、為需要的人送上溫暖。「我好想,可是我做不到,我覺得很無力。」正因為比別人更能同理這世界的痛苦,她也感到痛苦。也許就像作家蔡嘉佳[註1]所說的:「很多人以為憂鬱症是厭世,其實,他們比任何人都愛這個世界。」
為什麼會有憂鬱症?
從K開始,我開始研究、閱讀和思考,為什麼人會感到憂鬱?為什麼人用了憂鬱症的藥物一定要有那麼難受的副作用?為什麼快樂不該屬於這樣溫暖的人?
從生物醫學的角度來看,大抵上是腦中的神經傳導物質(例如血清素)的量太少[註2],導致人感受不到快樂。
從心理的角度切入,憂鬱症可能是人傾向看到自己壞和差的一面,並在這樣低潮的情緒中,更容易聯想到許多負向的經驗,如此惡性循環。最後變得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思緒、自我價值感低落。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在身處的情境中得不到抒發、或是長期處於某種壓力、壓抑的狀況,而對於無法改變的現況的無力,讓這個情境中的人感到欲振乏力,最後可能在此情境下而有了憂鬱症。

photos放大顯示
憂鬱症的解藥?
現行醫療用了許多藥物,來刺激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或是讓它們存在大腦久一點,不要讓快樂的感覺那麼快消失。但是伴隨而來的,身體其他部位也有許多藥物會影響的受器,很容易帶來為數不少和不輕的副作用。簡單來說,抗憂鬱的藥物像是散彈槍,可以攻擊憂鬱症,但是也無意間傷害到自己。「我覺得我的腦袋開始變慢,我逐漸失去引以為傲的思考能力。」「我失眠,我感受不到情緒、我容易忘記東西。」K 說。
而在心理諮商方面,也有認知行為治療,從當事人的家庭、成長背景或是看待事情的方式逐步剖析,找到認知中糾結的某個點,並透過談話和一些練習帶領當事人去思考不同看待事情的方式。
現在憂鬱症的治療方式因人而異,選擇看精神科的會服用藥物治療;選擇諮商的會接受認知行為治療,也有一些用電療的案例存在。不過大抵上憂鬱症還是難以用單一方式完全治癒,雖然透過心理治療和藥物可以得到控制,但是在成效上每個人都不同。
社會對於憂鬱症的態度?
接下來談社會對於精神疾患的不友善。作家林奕含[註4]回憶道:從政大休學前,她拿著診斷證明,向系主任解釋為什麼沒辦法參加期末考,他回應道,「精神病的學生我看多了,自殘、自殺,我看妳這樣蠻好、蠻『正常』的,」系主任接著拎起診斷書,說出林奕含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9個字,「妳從哪裡拿到這個的?」
大眾其實對於精神疾患普遍不了解,甚至是大學教授可能也有對精神疾患的刻板印象。精神疾患其實看起來跟正常人沒有什麼不一樣,他們易碎的不是外表的模樣,而是內心。
當他們鼓起最大的勇氣,跟其他人坦承自己的精神疾病之後,換來的不是同理,反而是質疑與不了解。這樣負向的循環下,大眾越來越不了解精神疾患的內心和處境,精神疾患的人也越來越不敢跟他人坦誠自己的病情,一旦坦承了,就好像做錯事一般,不但沒有得到安慰,反而還會被人從頭到腳審視一遍,心想著:「怎麼可能?」但他們最需要的,其實是接納和理解,至少不要被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我們所學的,不要用一本書的封面而斷定書的內容,顯然沒有運用在對於精神疾患的了解上面[註5]。所以傷害更深、誤解更深。情緒沒有得到抒發,像是陳酒一般釀在心裡,久了,難過會烈到讓人失去理智、失去過去所有相信的價值。「死」常常是他們最好的開罐器。

photos放大顯示
對於憂鬱症,我們可以做什麼?
「結果找一個我信任的人還比治療師有效。我從來沒有和治療師坦承我的恨,你是第一個讓我說出來的人。」某天跟K聊完,她這麼跟我說。
以自身和K相處的經驗來說,我們其實很難幫憂鬱症的人做到什麼,但是陪伴絕對會是一種力量。因為陪伴的過程中,他們可以感受到你的善意和溫暖,願意把他們心裡的話跟你分享。這很重要,因為他們不再是一個人面對這世界對於憂鬱症的不友善。
除了陪伴之外,我們也可以看看精神疾患寫的書籍,了解到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還有遇到的困境與掙扎是什麼。或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切入點,雖然沒辦法為他們平反所有不友善的事情,但至少我們能夠透過書籍去同理他們的心情和處境。理解和同理,會是社會對憂鬱症友善的第一步。
我覺得生活每天都是從負的開始。」我的朋友K常常這麼說,說憂鬱的日子好難受,每天都在想著怎麼結束自己的生命。和K聊著聊著,也看了幾本精神疾患書寫的書籍, ...
抑鬱症患者要堅持吃藥。 ... 這會是3億5千萬憂鬱症患者的福音嗎? .... 這些脈衝刺激抑鬱症患者大腦中功能減退的部位,看來有效。 .... 呼籲:讓家庭醫學科上第一線 · 如果你不會逼腳有殘疾的人奔跑,就別叫憂鬱症患者「看開一點」!
當憂鬱症的人遇到遭到異樣的眼光,或是聽到有人訴說著憂鬱症就是心理有問題、不夠樂觀啊、一些躲避藉口的那些話,如果你比其他人更能理解 ...
我們其實很難幫憂鬱症的人做到什麼,但是陪伴絕對會是一種力量。「我覺得生活每天都是從負的開始。」我的朋友K常常這麼說,說憂鬱的日子好難受 ...
從心理的角度切入,憂鬱症可能是人傾向看到自己壞和差的一面,並在這樣低潮的情緒中,更容易聯想到許多負向的經驗,如此惡性循環。最後變得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思緒、自我價值 ...
2017年5月9日 — 從心理的角度切入,憂鬱症可能是人傾向看到自己壞和差的一面,並在這樣低潮的情緒中,更容易聯想到許多負向的經驗,如此惡性循環。最後變得沒辦法控制自己 ...
2022年6月30日 — 憂鬱症是導致晚年殘疾的主要精神疾病之一。老年重度憂鬱症(major ... 但由於憂鬱症與衰弱症的症狀有部分重疊,使得憂鬱症患者可能會比非憂鬱患者容易 ...
憂鬱與憂鬱症最大的差別在於憂鬱屬於正常情緒反應,而憂鬱症會有有自我傷害的行為。依照憂鬱症嚴重程度的不同,可以分為輕度憂鬱、中度憂鬱、重度憂鬱。輕度憂鬱症患者雖然 ...
有些患者的憂鬱症發作(英語:major depressive episode)時期分為好幾年,可能有段期間與常人無異,但其他時間一直出現憂鬱症症狀。重度憂鬱症會對日常生活、工作、教育、 ...
2022年7月5日 — 憂鬱症是導致晚年殘疾的主要精神疾病之一。老年重度憂鬱症(major depression)的盛行率從4.6% 到9.3% 不等,亞臨床憂鬱症(subthreshold depression ...
隋棠美工刀dcard王心凌新歌中 高齡 憂鬱症劈他的雷正在路上憂鬱症先天後天憂鬱症想開一點劈你的雷正在路上dcard跟憂鬱症的人相處好累劈你的雷正在路上ptt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舞蹈 醫療 出口值 突破拔智齒矯正dcard午休美容 痕跡
秋冬腦中風增!翁已2度中風不自覺開車失控撞@newsebc-YouTube
進入秋冬是腦中風的高危險期,尤其氣溫下降,血壓升高,比起夏天,近期的腦中風患者,就增加兩三成,有些患者之前可能小中風...
和黃醫藥(00013)血液惡性腫瘤藥物展開I期臨床試驗-鉅亨網
《經濟通通訊社7日專訊》和黃醫藥(00013-HK[1])公布,在中國啟動一項新型抑制劑用於治療血液惡性腫瘤的I期臨床試驗。首名...
隱形殺手:胰臟癌(一)-施蘊知醫生-腸胃肝臟科-信報網站hkej.com
2024年5月29日施蘊知醫生[1]腸胃肝臟科[2]何先生年約50歲,最近半年常常感覺飯後有飽滯感。他以為工作忙碌及食無定時引致。...
冬季養生如何食補?呼吸道疾病患者能吃膏方嗎?中醫專家養生節上“劃重點”
中醫講究天人合一,四季特點是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四季養生對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今天上午,由上海中醫藥大學...